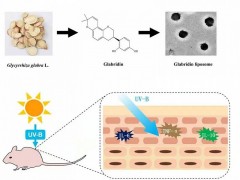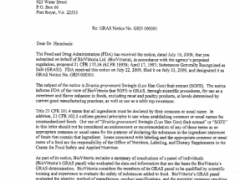由于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实质等同”原则其实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有位朋友推荐我阅读了2014年6月15日发表在Food Chemistry中的一篇文章: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soybeans on the market: Glyphosate accumulates in Roundup Ready GM soybeans(市场上大豆成分的差异:草甘膦在抗农达大豆中的积累)。这里的抗农达大豆就是具有耐草甘膦特性的转基因大豆。这篇文章对美国爱荷华州31个批次大豆中除草剂和杀虫剂的残留进行了测定,并描述了大豆的营养和元素组成。大豆样品被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别:(1)耐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GM-soy);(2)采用传统化肥种植方式的非转基因大豆;(3)采用有机耕作方式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文章得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结论: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高残留的草甘膦和氨甲基磷酸(AMPA,草甘膦在植物体内最常见的代谢产物)(分别为3.3和5.7mg/kg),不同农业耕作方式生产的大豆其营养品质是不同的,有机大豆显示最健康的营养成分,有更多的糖类,如葡萄糖、果糖、蔗糖和麦芽糖,更多的总蛋白质,而含较小的锌和纤维。有机大豆还含有更少的总饱和脂肪和总ω- 6脂肪酸。本研究否定了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是“实质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的。而且,作者还充满信心地说:如果采用35个不同营养和元素变量来描述各大豆样品的话,我们完全能够毫无例外地区分出这三种不同类别的大豆,说明那些准备上市(ready-to-market)的转基因大豆其成分特征与传统种植和有机种植的大豆“实质不等同”(substantial non-equivalence)。
论文很长,在这篇博文中无法全文翻译。但我抽提这篇论文的前言、讨论和结论部分,按照我的理解对文章进行了重新整理,组成了一篇博文。如果对具体的实验设计和数据报道有兴趣,可直接阅读原文。
在全球范围内,耐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是转基因作物无疑是最多的。除草剂草甘膦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2008年生产62万吨。2011年世界大豆产量为2.5亿吨,其中主要生产国美国占33%、巴西占29%、阿根廷占19%、中国占5%、印度占4%。在2011–2012年,种植大豆约3千万公顷的美国,转基因抗农达大豆占93 - 94%。其他主要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分别占83%和100%。在全球范围内,抗农达大豆转基因大豆在2011年占总产量的75%。
第一代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由孟山都公司开发的专利,在整个生长季节都暴露在草甘膦农药中。在1999年早期对研究中,研究人员当时对转基因大豆的成分分析并不是针对喷洒除草剂的植物进行的。不知道这个错误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不久针对喷洒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进行再次测试,当时的结果宣称与非转基因大豆实质等同。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却没有测量除草剂的残留量。按照实质等同的概念,既然宣称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传统作物的营养和元素是相似的,有同样的营养成分,因此与传统植物食品一样安全。然而,在鉴定这种安全性的成分研究中忽略(不测量)农药残留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存在化学残留,显然是很重要的问题,首先这些化学残留明显是植物组成的一部分,其次它们对最终的植物产品增加了毒性,要么自身添加,要么影响植物的新陈代谢。一般来说,OECD所建议的主要食品和饲料的营养是需要对大豆新品种进行安全评估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估集中于转基因作物本身的致敏性和毒性,或者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转化过程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很少关注除草剂残留及其代谢物可能积聚在最终的产品中,以及是否接触这些除草剂或其他与基因改造所导致的本身功能改变(改变了转基因植物的中间代谢过程)可能会影响其营养和元素组成。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了草甘膦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其中转基因大豆为主。因此美国转基因大豆暴露在草甘膦下的农业实践,可用于测试喷洒草甘膦是否可导致化学残留物的累积,以及最后大豆产品的成分差异。这里进行残留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并没有检测转基因作物中主要农药的残留。与来自市场的真实样品相比,用于科学研究的转基因作物往往控制在小实验区的范围内。在大多数研究中,省略了施用除草剂的环节,或者施用的剂量低于农民常用的剂量,因此这些测试材料并不能代表实际情况中的典型农业作业。有关草甘膦施用率与大豆营养成分之间关系的知识是很缺乏的。一项研究发现草甘膦施用的转基因大豆与α-亚麻酸(ALA)和铁离子含量减少、油酸增加之间的联系。与具有相同基因的常规大豆品系相比,转基因大豆的植物雌激素水平下降12 - 14%。也有人发现,转基因大豆可能比传统大豆有更高或更低的异黄酮含量。
植物内源EPSPS(5-烯醇丙酮酰莽草酸-3-磷酸合酶)对某些必须的芳香族氨基酸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即苯丙氨酸、色氨酸及酪氨酸通过莽草酸途径的合成。除草剂的活性成分草甘膦可以绑定到所有已知植物、杂草和作物中。这种绑定会导致EPSPS酶的失活而引起杂草死亡。市场上使用的转基因大豆,其耐除草剂性状是通过转基因插入,让植物表达农杆菌属菌株的类似物EPSPS,而草甘膦绑定到转基因大豆中的EPSPS是一种浓缩的非抑制构象。因此转基因植物表达出EPSPS酶产生耐受草甘膦的性状。农民可能为根除各种杂草而喷洒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并不会受到伤害。然而,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大量使用草甘膦,可能导致杂草种群的变化并选择出抗草甘膦的杂草。反过来这触发了更多、更高剂量草甘膦的施用,进一步促进草甘膦抗性杂草的进化。这种螺旋式的竞赛对农民来说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但也可能通过植物组织积累草甘膦残留而影响消费者。抗草甘膦的进化是非常糟糕的,尤其对美国来说更是如此。缺乏多种杂草管理实践,仅仅依靠除草剂进行单作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脆弱性产生。
文章对草甘膦施用的生态学效应和环境影响也进行了分析。
(1)草甘膦可以被整个植物吸收并移位,叶片和豆子中都发现了草甘膦。然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没有根据草甘膦残留来区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植物。而孟山都公司则声称,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低于传统大豆(草甘膦残留为16–17 mg/kg,可能是收获前刚刚喷洒的缘故)。1999年,孟山都公司测定转基因大豆所记录的最大残留水平为5.6mg/kg,这代表了“极高的水平,远高于那些通常的水平”。而本研究中,10个转基因大豆样品中有7个样品超过了这种“极端水平”,说明目前正在向更高残留水平发展。美国日益增加的草甘膦施用量和抗草甘膦大豆普遍种植,导致抗草甘膦的杂草被选择出来。
(2)重复多次喷洒农药和生长季晚期喷洒会导致农药残留的增加。有研究表明,在开花的时候喷洒农药比生长季早期喷洒会增加草甘膦5到10倍,AMPA增加10到25倍。而在生长季晚期喷洒农药似乎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了惯例。已经证明,草甘膦可减少转基因大豆的光合作用和营养吸收,不管是在温室和田间试验,还是对第一和第二代抗草甘膦大豆植物都是如此。高草甘膦施用减少了alfa-亚麻酸但增加了油酸,也就是说产生了不健康的脂肪酸。草甘膦也可能改变微量营养物质的状态,特别是锰和锌,这取决于土壤类型。一般来说,植物根际的微生物群落健康与否,对于植物健康是一个重要因素。草甘膦是有可能影响植物生长所赖于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如增加镰刀菌属。AMPA是温和的植物性毒素,会降低大豆的光合作用和蒸腾速率。草甘膦除草剂的其他成分对转基因大豆也被认为是有害的。
文章还强调,草甘膦相关的毒性和健康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他的研究声称,草甘膦不会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发育与生殖,但其中的表面活性剂可能导致一些毒性效应。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深入讨论,一些证据表明草甘膦本身是一个致畸原,而其中一些常用佐剂放大了这种效应。
最后,文章还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1)从市场中增加采样和测试作物;(2)测试长期饲养中化学残留物的剂量反应效应;(3)在风险评估的监管系统中应包括农药残留测量和安全检测;(4)进一步研究除草剂和杀虫剂的间接生态效应,即对土壤种群的生态学相互作用,以及对营养吸收和植物成分的可能影响。
(作者:赵斌) 文章来源:科学网